王怡霖作為一名香港大學博士生,她選擇中國秀場直播作為她的博士論文研究,並進行了為期三年的田野調查。在直播行業中,女主播們在線上與觀眾互動。然而,她們的生活並不如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美好。她們長時間曬不到太陽,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繫,導致身體健康問題和心理壓力。此外,主播們還需要面對觀眾的控制和要求,為了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打賞,她們可能會接受各種難以接受的挑戰和懲罰。王怡霖也逐漸接受了這種系統的「規訓」,並開始積極迎合觀眾的需求。
在王怡霖的研究中,除去當紅主播,能持久留在秀場直播行業裏的主播多為社會資源較弱勢的女性。而「大哥」們則試圖在線上填補一些線下生活的空白,或為了排解在異鄉的孤獨感、或釋放晝夜顛倒的工作壓力、或渴望親密關係……主播和「大哥」在直播間相遇,當現實世界不能滿足他們時,欲望、角逐、操控、討好在秀場內前仆後繼。
王怡霖表示,起初她還會觀察每一個進直播間的觀眾,筆記記下他們喜歡甚麼、點了甚麼歌,觀察主播和觀眾之間的互動。後來,她像其他主播一樣,為了持續在秀場直播中存活下去,拿到更多分成,彷彿漸漸接受了系統的「規訓」,滑入一種積極開播、接受PK懲罰、討好觀眾、渴望打賞的狀態。
她說,初初當主播她曾按「公會」建議找人PK以「豁出去」增加人氣。她找到一男主播,對方人氣較高,「PK」輸了要跟着他做動作,本來覺得「沒很過分」,後來才發現那些動作在鏡頭前具「性意味」。還有一女主播和她PK時,對方提出「得玩得起」,比如誰輸了,就往衣服裏面倒水。一名女主播也坦白,「大哥」是指支撐起主播大部分收入的忠實粉絲。輸掉比賽時,大哥想出一個懲罰方式,要求她用腳抓起一個小球。這種奇怪的癖好讓她覺得很噁心,但她找不到第二個男人,比這個大哥更能花錢。做完懲罰,大哥就會給她刷一個禮物。
看主播被羞辱,是娛樂的一部分,所以別人才會願意花幾千,甚至幾萬刷禮物。一個平台上的玩家告訴她,在直播間裏,當着其他男玩家的面罵髒話、挑逗女主播,操控她們做自己想讓她們做的事情,會讓他覺得很釋放,很舒服。
女主播收了「禮」就要回報,給送禮人表演,不管是打屁股、下蹲,還是對着椅子晃,給送禮人及時的反饋。
有的女孩鋌而走險,跟她們的重要支持者建立了線下的親密關係,但是那樣的關係最終變成一段段慘痛的人生教訓;還有精神上的影響,內心壓力很大,長期有不安全感——這是要獲得別人喜歡才能賺錢的行業,是討好型的。
如果發現大哥關注其他人,很多主播會註冊匿名小號,跟蹤她們的大哥。每天截螢幕保護程式存大哥主頁資訊的財富值,如果數字有變動,就能推測大哥在別的女人那裏花了多少錢。
就像妻子發現丈夫的外遇證據一樣,她們會和大哥鬧翻,或者要求大哥送更貴的禮物作為補償。來自上海的25歲大主播佳佳,故意一週不直播,拉黑大哥的賬號,讓他知道自己吃醋、生氣,回來哄她。更極端的時候,她連續三天不間斷地直播,用這種挑戰身體極限的方式,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間——刷夠禮物,大哥就有權讓女主播休息。有的女主播,經受不住連續直播,會在鏡頭前暈倒,給男性玩家最強烈的情緒刺激。
很多女孩做了主播後,會很不適應線下的生活。它對人的親密關係、價值觀,人能接受的生活模式、工作模式,都有很大的改變。有的女孩習慣了坐在直播間跟人說話、互動就能收到禮物,但在現實中掙一份錢很難。
王怡霖說了以下一番很感性的反省:
下播之後,我躺在床上,耳朵剛被那些低音炮網絡神曲轟炸了幾個小時,隱隱發痛,聽力下降,大腦卻變得更活躍。我也開始失眠,被一種巨大的失落感淹沒:明天那些人還會不會來?還能不能收到禮物?無論獲得了甚麼,有多麼開心,一覺醒來,一切都可能隨時失去。做這行久了,人的注意力、精力,都會被平台吞噬,對真實的生活提不起興趣。我每天都會感到巨大的空虛感,但還是不受控地打開直播平台,連看本書來充實自己也做不到。很多主播告訴我,以前還會刷劇、看綜藝,做了主播後,再也沒看過了。四五個月後,儘管我播得不錯,但我還是意識到,這種生活不能再過下去了。
我論文寫完,也還沒完全走出來。我覺得這是太獨特的一份體驗,真實地感受到這個體驗對人的改變。我會想起自己接觸到的那些女孩、男性玩家、公會裏的人,那位打自己巴掌的女主播,看着讓人難受,那個畫面一直在我內心。
平台更新發展很快。作為研究者,我們可以退出,可以只作為旁觀者,決定要不要進入、分析、寫些甚麼。但對於很多人來說,他們是被動地捲入其中。我不想承認的一點是,在我的研究中,對很多主播來說,做直播是他現有所有選擇裏面相對更好的。
有時候我沒辦法對這個東西很樂觀,或是忘記之前的那些體驗。因為我覺得忘記也對這個研究挺不負責,還是希望記住,然後有更多學術上的討論,能帶來一些影響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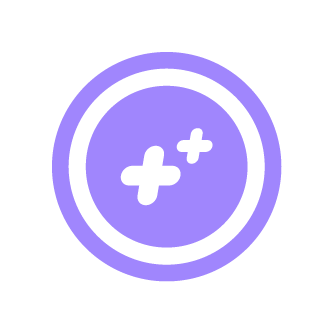
/public/article/images/202401/ed518fe7-957f-4097-b182-d1cb834c28d2.jpg)
